.jpg)
 AKI_kikumugi/status/1633135080343486465
AKI_kikumugi/status/1633135080343486465重制版前言:本文为本系列首篇角色关系的联动专栏《忠诚的尸体——宫古芳香(原型整理探讨、深度考察与圣地巡礼)》的重制,在念及《重制版:穿墙的邪仙——霍青娥(「原型之上的原型」文本探讨与零设巡礼考察)》全面重制与后续内容增补已然完成的同时,顾虑到旧版芳香专栏对于旧版青娥专栏的内容补充,而旧版芳香专栏的部分观点与文本分析的确过于武断,在新框架新大纲的基础上进行原型文本考察与论文观点整理,圣地巡礼部分则选择更为契合芳香原型的巡礼地,旧版芳香专栏将在重制版审核发布三天后的第一时间内进行删除。
好的,以下为开年来第二篇重制版专栏的注意事项;
本文为重制版的《东方神灵庙》三面角色「宫古芳香」的原型整理考察探讨与圣地巡礼。皆因笔者对于2021年3月发布的旧专栏不甚满意,特此修正常识性谬误与错引论文的段落摘录,重新整理旧有情报与个人观点并发表。皆出自当代民俗学视角对于角色原型文本多角度多方面的路径,经由ZUN在《神灵庙采访》和《东方外来韦编 2019 Spring!》在角色设计之时所阐述的评价,考析针对当代泛ACG文化领域的各类僵尸捏他分析和八十年代港台「灵幻僵尸片」研究,溯源至近古时期民间志怪文学「尸变型僵尸」的文本嬗变,从而比对「亡者归来/活着的尸体」型的跨文化叙事,辅以「宫古芳香」名称来源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虚构变迁;对本文疏漏之处存在不同见解的各位,欢迎来评论区交流。
本文所援引的研究论文的摘录观点,或将涉及以现代民俗学为首的戏剧与影视学、古典文学、文献学、比较文化学、象征人类学、现代心理学、宗教学等各方面学科视角的研究论文,及笔者个人观点注释,论文标题和作者情报均放置在正文内容,倘若在正文中援引论文时看到除却章节开头外的非大段引用摘录的个人注释,文字颜色会稍稍变化,还请各位观看时多加留意。
本文参考的诸多资料,均来源于THB WIKI、东方元NETA WIKI、ピクシブ百科事典、ニコニコMUGEN WIKI、日文WIKI、知乎、推特、知网、万方、爱学术、钛学术文献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IDATA、百度学术、谷歌学术、CiNii、J-STAGE数据库、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怪异.妖怪数据库等门户网站。
针对本文中提及的存在于大陆境内的「东方圣地巡礼/东方舞台探访」感兴趣的各位,敬请私聊主动联系笔者,笔者会尽量提供你所在省份区划内的东方角色原型巡礼地与交通方式、追加情报等,多少为芳香后续二创题材的丰富让创作者拥有实践灵感体验的机会。
東方本身是宗教民俗的戏说,二设又是東方的戏说。

 artworks/38694437
artworks/3869443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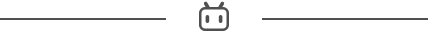
STAGE 3 命蓮寺墓地
直線の楽園
直线的乐园
栖息在墓地的,究竟是人是幽鬼还是妖怪
被大家称作神灵的这些灵为何会涌向墓地?
三面BOSS 忠诚的尸体
宮古 芳香(みやこ よしか)
Miyako Yoshika
种族:僵尸
能力:什么都能吃程度的能力
BGM:リジッドパラダイス(Rigid Paradise)=僵硬的乐园

其一 港式「吸血僵尸」的影视形象研究
首先,据《东方人妖名鉴 宵暗篇》的芳香的角色评价条目中ZUN所提及的「因为道教也是主题之一,所以就设定成了僵尸」,为何ZUN会认为道教与僵尸有所联系呢?针对上述疑问,在旧专栏编撰时期的笔者忽视《神灵庙采访》中ZUN亲口承认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的港台「灵幻僵尸片」的直接影响,较多以他者化视角看待道教诸南传法教的仙术集合民间志怪印象认定为形象设计来源,完全脱嵌于ZUN笔下以港台「灵幻僵尸片」当中的「吸血僵尸」形象为原型设计的「宫古芳香」。
其次,笔者检索过的芳香相关角色解读文本的多数文章中,以道教与都良香的关系所展开话题,而僵尸种族的表象设计却几乎无人涉及,分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的「吸血僵尸」形象的背景之下针对传统清末志怪观念的解构,更是大众印象中更为熟悉的「僵尸」形象建构的一环,通常被描述为肢体僵硬、力大无穷、青面獠牙、身穿清朝官服、额头贴黄符、通过特殊茅山术使役或退治的「吸血僵尸」 。就据清末各地域民间志怪文本角度来说,「吸血僵尸」形象既是取材自清末民间志怪的情节母题,又是近现代香港受到西方怪异情境母题的影响写照,导致原本民俗语境中的各地域志怪间的模糊化僵尸形象被锚定,而元文本不存在一个可供被集体记忆描述的僵尸形象,通过近现代香港社会现实环境的拼接与改造,民间志怪与「土洋结合」互动过程中的想象力再塑造,从而实现元僵尸文本创作的再定义化。
您有看过僵尸的节目吗?ZUN:有看哦,在学校的时候扮演僵尸的游戏也很流行呢。原来电影《灵幻道士》非常流行,后来《幽幻道士》系列之类的电视剧又流行起来了呢。记得是《来来!僵尸》吧。ZUN: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仿佛是从《灵幻道士》派生出来的作品。在当时是一个风潮呢。但是,在那之后的僵尸也就《恶魔战士·吸血鬼猎人》里的泪泪了吧。在我的心中泪泪的印象特别深刻,最初本想把芳香设计成动作更加机敏的拳法家之类的形象,但那实在是太俗套了。泪泪怎么说都有一种非常干练的印象,因此我觉得设计一个脑子烂掉了的角色比较好。——「神灵庙采访」
墓地里有僵尸,这种设定已经别用烂了。这一关全是墓碑,制作上就很麻烦,线香的烟雾的效果也是一样,若是没这个效果场景就不像墓地了,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了出来。说老实话,僵尸并不适合做进游戏里吧,要怎么才能打倒已死的僵尸,这一问题的答案从结果上来看已经被带到4面去了。——《东方外来韦编 2019 Spring!》东方神灵庙全关卡 Cross Review
按照上述访谈,或许可整理出在ZUN印象中的,港台僵尸片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的日本社会环境的文化影响脉络,所提及的《灵幻道士》与《幽幻道士》,分别是香港影坛寰亚影视在1985年发行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灵幻僵尸片」——《暂时停止呼吸》(港名:《僵尸先生》),在黄鹰《中国第一具僵尸》一书中,曾写道:“因为 《僵尸先生》的成功...港台部份制作人于是一窝蜂的抢拍 ,有一纪录十七部僵尸电影同时赶拍...”,以及后续台湾影坛金格影艺在1986年发行明确翻版跟拍的TV剧《僵尸小子》,《僵尸小子》为缓和《僵尸先生》的喜剧复合恐惧的氛围,尽管《僵尸先生》喜剧元素已较为明显,但《僵尸小子》多以喜剧类元素取代之改动整体框架,注重人物关系塑造的特点。导致《僵尸小子》虽在环华语圈的评价较为一般,换来的却在日本上映后的高热度,访谈中的《来来!僵尸》正是1988年日本TBS电视台出资请金格影艺所拍摄的《僵尸小子》同一世界观之下的日语配音版的本土化TV剧。
况且检索日文WIKI的「キョンシー」词条介绍与探讨「灵幻僵尸片」对日本影响的新闻专栏报道,似乎在日本人视角的认知中存在一条起始于1985年的《僵尸先生》——1986年的《僵尸小子》——1988年的《来来!僵尸》如此明晰的荧幕形象脉络,相当于在日本人视角看待的「吸血僵尸」本就是建立在堆砌而成的「灵幻僵尸片」之上的再塑造的景观产物,并非是传统大陆视角去看待「灵幻僵尸片」之时,认为僵尸正是承袭清末志怪与民国戏曲的土洋结合产物,日本针对僵尸文本的多数误读大抵由此而来。

与此同时,香港僵尸电影仅在僵尸呈现的影视形象上采纳西方吸血鬼青面獠牙、咬人颈脖的特征,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植根于香港本土民俗的焦虑情绪,从而开创灵幻僵尸片这一品类,据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庆席导演」于2019年所撰「《僵尸先生》的狂欢化叙事」,文中认为:《僵尸先生》起码融合恐怖、功夫、喜剧、爱情四种类型模式。故事的基本 架构可以总结为求救者 发出求救信号,拯救者(九叔)接受任务,与反派(僵尸)斗争,最终战胜反派,这一基本架构为之后的僵尸片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士降服僵尸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都是一些传统民俗中常见的器物,如糯米、八卦镜、桃木剑,使得这一恐怖类型融入不少东方民俗趣味。而“中国香港的僵尸电影只是功夫片的借尸还魂”则一语道破僵尸片中功夫元素的突出性。
影片中的僵尸身穿清朝官服, 吸血、走路一蹦一跳,这一形象明显受西方文化中的吸血鬼的影响,香港早期僵尸片的僵尸几乎完全就是吸血鬼的翻版,而《僵尸先生》的英文片名为《Mr.Vampire》。剧中的僵尸形象显然是建立在清末民间志怪与民国僵尸戏曲的传统基础之上的,不过就僵尸用獠牙吸食鲜血这一点而言,则明显借鉴吸血鬼的特点。无论是“僵尸”还是“吸血鬼”,其形态都是一种非常态的“怪诞身体”,“通过怪诞的方式走出了严肃身体的牢笼,从而实现一种身体与身体的对话”。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共通性上,《僵尸先生》继承自《鬼打鬼》开创的以“茅山道士”的形象作为秩序的维护者,与僵尸对立的模式,从而完成了对西方传说中“牧师(驱魔人)对抗吸血鬼”的故事原型的移植,毕竟中国关于僵尸的传说,并不存在这样与僵尸对立的驱魔人型的角色。而林正英所扮演的“茅山道士”,则以其正直的性格,棱角分明的脸庞、一字眉等特点成为中国香港僵尸片的象征图谱。
民间节日的狂欢需要一个活动的场所或表演的舞台,这也是非现实世界得以成型的空间因素,是全民性的笑得以产生、相互感染的基础。狂欢节中心的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代入狂欢与广场场域的视角看待的话,影片中的“义庄”是宗族社会的产物,由宗族出资建造,为族人提供祠堂,学校等场所,亦有影片中“停尸”的功能,因而具有一种公共属性,允许不同的人在此汇聚并“对话”。在影片中,汇聚于义庄的不仅有赶尸先生和他的十几具僵尸,还有女鬼、军官表哥和任家大小姐,在此地上演了人尸大战,尸尸大战,人鬼大战的疯狂戏码,义庄成为汇聚全民的“广场”。
姑且以这篇论文参考的「喜剧僵尸片」所提炼引用出的「狂欢化广场」理论模型,重新整理视角来看待《东方神灵庙》本篇故事的话,是否梦殿大祀庙本身就能算是一个「狂欢化广场」?反复上演人类与神灵、妖怪与神灵、圣人与人类的戏码,但故事有没有港式灵幻喜剧僵尸片的味道就相当见仁见智。
在杨杰所撰的《浅析香港僵尸电影题材之来源》一文中即认为香港「灵幻僵尸片」的建构来源在于西风东渐、取材于民俗、土洋结合,原本系为吸血鬼电影题材的本土化表征:香港僵尸电影的首次转折始于1957年由王天林指导、陈厚主演的《湘西赶尸记》,这部电影讲述以湘西赶尸为名,勾搭贩毒的故事。《湘西赶尸记》把民俗中的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思想及湘西赶尸代表的「刻板印象造就的新民俗」融入到香港僵尸电影中,使香港僵尸电影开始缓慢地发育并渐渐本土化。可记为僵尸电影的第二次本土化演变,可喜的是,这次的演变逐渐深入到文化层面,也正因如此,这部电影获得阶段性的成功。对于第三次本土化演变,笔者认为是1979年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茅山僵尸拳》,该电影由香港武师刘家良担任导演和武打设计,在电影中融合武打、喜剧等元素,并且首次让电影中的僵尸穿上本土化的清朝官服。《茅山僵尸拳》以幽默剧情和精彩武打桥段获得观众认可,成为香港僵尸电影的奠基之作。《茅山僵尸拳》的成功标志西方吸血鬼电影本土化的成功,善于借鉴和融合的香港电影人终于拍摄出有自己风格的僵尸电影。
笔者认为,想解构香港僵尸片其必备的元素为:主角僵尸、道士、徒弟、南传法教的茅山术、道士武术动作及师徒矛盾所产生的喜剧效果,以致造成许多人对于道教的映像除武当太极张三丰,就是茅山捉鬼林正英。主角多为法师徒弟,一般是有勇无谋、武功平平的滑稽角色,但却经常能 够化险为夷,而法师则更像是权力代表和行使者,通过法术对付僵尸,让一切回归平衡。由此可见,僵尸更像是闯入者和破坏者,他的出现意味着秩序和规则打破,更多被用于制造故事冲突和转折。
因此,僵尸片是一种混合状态,而非独当一面的类型,特别是「功夫僵尸片」与「灵幻功夫片」一脉相承的情况下,要去主动区分则是相当模糊化的存在。通常在「灵幻僵尸片」中所饰演的主角僵尸,虽代表着原欲、非理性,但却因被处理成永远的失败者而充满戏谑性的具体意味,因「吸血僵尸」形象直接取材本土化于西方吸血鬼电影题材,「灵幻僵尸片」是否同样继承前者的反文化含义以及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的问题呢?特别关乎影片所展现的时代背景压抑欲望的直接表现反应,笔者认为是肯定的。
简单理解为「吸血僵尸」形象的成型,反而变相扼杀传统志怪中丧葬风俗联系紧密的尸变而成的僵尸形象,本应更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库,针对大众印象中僵尸概念进行的框架再塑造与再输出,八十年代后半至九十年代前半的僵尸热潮在影视类领域的野蛮生长,相当给大众观影市场确立「灵幻僵尸片」只能照着前人已然搭建好的一言堂去进行拍摄,等同把「灵幻僵尸片」中那股子恰到好处的位于土洋结合框架的叙事文本,逐渐导向于固定范式内部的各类死胡同,多数观点认为「灵幻僵尸片」题材在九十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颓势,无法迈向于新题材与新时代的,应视为「灵幻僵尸片」完全倾向于吸血鬼题材化后的内因。

再者说,主要因《僵尸先生》引发的僵尸电影热潮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的港澳台与日本、大陆市民阶层的集体记忆,而「灵幻僵尸片」品类几乎是伴随林正英式僵尸电影的盛与衰,在这之前呢?诸如「吸血僵尸与吸血鬼」存在设定借鉴的关系,回顾「僵尸喜剧」的影视映像历史,「吸血僵尸」前的僵尸形象在香港早期僵尸电影中,整体呈现条僵尸形象元素再建构的趋势,援引「赵轩副教授」于2016年2月发表在华文文学第133期的文学论文《香港僵尸喜剧 :延异型叙事与文化“撕裂感"》文中观点:港产僵尸电影从出现伊始便与喜剧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套路,而身着清朝官服、行动高度拟态化的中国僵尸则一度成为香港影人独创的视觉形象。20世纪70年代末,民初功夫谐趣片开始走下坡时,洪金宝以茅山道士的民间志怪传说与民初功夫片混合而成的《鬼打鬼》,主要讲述两位茅山道士斗法的故事,在使得两种类型片再度流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首位把茅山道士、茅山术与僵尸混合为一,使之成为僵尸片的重要特征之一。
而《茅山僵尸拳》与《蛇形刁手》(1987年)如出一辙,以奇妙事物的拟态化动作作为武术设计的来源,影片令僵尸双手平举、蹦跳行进,并且以此创设拳法,更将赶尸术与武术动作相混合,形成独特的动作奇观,同时还第一次让僵尸穿上本土化的服饰——清朝官服。这部并不纯粹的僵尸电影 ,实质为之后的僵尸喜剧创制基本的动作规范和造型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清朝官服”实际上是民国初期丧葬流行的所谓“中华寿衣”,并没有明确的时代指向,这一无心插柳的设置,最终却成为后世之作奉为圭臬的基本类型元素。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香港僵尸电影只是功夫片的借尸还魂。由于早期制作直接因袭象形功夫片的动作规范,僵尸形象的拟态化塑造和道士斗僵尸的打斗场面大都秉承功夫片的基本套路。出身于戏曲表演的龙虎武师,将戏曲表演中一板一眼的节奏感引入动作场面,加之功夫片的惯用音效,使得银幕上出现有如打击乐的节奏,短暂的停顿起把动作分段的作用,带来如同断音的效果。僵尸形象则因完全虚构,其动作规范类似戏曲舞台上的拟态化演出,一切以假戏假作为限,更使得二元对立关系中的另一方——道士仪式化驱魔作法的动作原则具备银幕合法性,进而双手平举、一蹦一跳的僵尸与拿姿作态、画符舞剑的道士成为早期香港僵尸喜剧的标准化视觉特质。
诸如影片中墨斗、桃木剑、黄符、鸡血、童子尿种种类似于游戏工具的物象,更让原本应当惊惧、紧张的降魔过程变成有着神秘主义氛围的奇观展示,可以说花样百出的茅山术,使得上述喜剧性松弛转向了颇具仪式化意味的游戏性叙事,伴生于游戏性的,是僵尸喜剧自我解构的强烈自反性,这种自反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同类流行作品乃至影片本身的戏谑和反讽。真正支持僵尸喜剧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并非体现在喜剧性类型气质的开掘和积累,僵尸喜剧集中体现香港类型电影的延异型叙事和能产机制,本文作者认为每一部僵尸喜剧都在反讽、戏谑的过程中对于以往成功影片的叙事范式进行着擦除和消解。并且以自身的叙事努力建构出区别于前人新情节范式和类型元素 ,这就使得僵尸喜剧始终处于一个产生差异的运动中,进行不断自我擦除、消解并衍生新元素的情节范式表现。
(其实这么阐述可能有点模糊,说白了就是在上一部灵幻僵尸喜剧中使用的退治僵尸的案例和道具,衔接到下一步作品中立马就无用不灵,时刻让电影院观众保持对于题材的新鲜感。)
上述不同于清末志怪的新奇元素的纳入,间接导致多数文本中动辄描述为宏大时间演变而成的清朝官服的「吸血僵尸」,其背景可以说是相当异质化的存在,而大众印象的僵尸们四肢僵直如麻雀般前进的姿态,先是《茅山僵尸拳》奠定主体印象后续却经由《僵尸先生》而发扬光大,另有说法认为僵尸姿态应为《僵尸先生》导演刘观伟的个人爱好塑造,笔者还曾听闻导演本身就是茅山道士或者导演亲戚为茅山道士的轶闻,然而根据上述整理可以得知《僵尸先生》之所以经典还是建立在前辈们的基础之上的存在。否则原本在清末志怪文学与民国初年民间戏曲的僵尸印象,更多被描述为异常灵敏袭击人类的存在,甚至可以认为「吸血僵尸」在这一时期只是香港剧作家笔下的附会中国志怪元素的「吸血鬼」。

另外,据南京大学张瑞文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尸变”类型电影中的形象研究——以“好莱坞吸血鬼”和“香港僵尸”为例》的电影批评观点为核心:僵尸成因的拓展也是《僵尸先生》对于僵尸形 象改造的一个方面。尽管整体上看《僵尸先生》中的僵尸己经不再具有早期西式僵尸——吸血鬼影片的外貌,但影片仍借鉴吸血鬼影片的一条重要规则,那就是被僵尸吸血后的人也会变为僵尸。无论是哪种记载或解释,僵尸成因都源自于尸变,而吸血传播并非成因中的一种。僵尸虽吸食人血,但并非如吸血鬼一般从脖颈吸血,目前可考的文字对于僵尸吸血的记载并不多,只在《子不语》中《僵尸求食》《僵尸吸人血》极少篇目中出现过,且均并非从脖子吸食。
《东方求闻口授》中的芳香评价曾经提及:「万一,要是被咬到的话就已经太迟了。虽然只是暂时性,但还是会变成僵尸而丑态尽现。更甚者,无意识地咬了别人,说不准自己也变成在帮忙一起增加僵尸同伴,光是这件事就不得不回避她」与《东方神灵庙》设定文档能力注释的「人类若是被她吞噬掉一部分的话会暂时变成僵尸」,或许是参考过上述僵尸吸血传播的而成为僵尸设定,毕竟同样在神灵庙设定文档提到「虽然她其实和丧尸差不多」。反而是「什么都能吃掉程度」的能力运用及符卡欲灵「Score Desire Eater」(贪分欲吞噬者)的回复HP的设计,倒是真有可能取材「吸血僵尸」形象,而《僵尸先生》中的僵尸不吸血无法维持行动的要素,互相为防止吸血的设定冲突,在《东方神灵庙》中简化为吸收欲望化成的神灵即可回复HP。
到此为止,宫古芳香的角色设计已然从属于港台「灵幻僵尸喜剧」的场域内成功解构出来,芳香原典的「吸血僵尸」应当视为香港本土民俗与清末志怪文学结合西洋吸血鬼题材形象的产物。可这又不禁引人好奇,香港本地的「灵幻僵尸喜剧」诞生或者催生的原因又是什么?香港剧作人们为何选择僵尸这一题材作为题材来设定呢?笔者因此认为,香港本土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得不提的,一是香港身为英国殖民地的文化孤岛时期的主体性危机的反应,而香港早期的套皮吸血鬼的僵尸片同样是在某段时间内同为文化孤岛的上海,将清末志怪僵尸和民国僵尸戏曲照抄吸血鬼电影的作品,在战争期间南下香港避难从而输入的结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灵幻僵尸片」特色成因的话,再据上文援引过的「赵轩副教授」在《香港僵尸喜剧:延异型叙事与文化“撕裂感”》文段中第三章节「混乱、焦虑与“撕裂”的文化心态」的观点:香港僵尸电影无疑将「混乱」这一主题进行 了更为具象化的时空表述,一方面僵尸喜剧普遍采用的民国初年背景,实质上正是军阀混战、礼崩乐坏的时代缩影,一系列影片中蠢笨无能的军阀官员,往往在僵尸面前束手无策,正表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失落与社会秩序的崩溃;另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坟冢、荒村、义庄、古宅,均是在空间一喻示文明社会的放逐,存在于上述破败空间的可怖行尸,自然具备导致混乱的合理性。
香港回归过渡初期神怪、恐怖的功夫喜剧的流行,基本与人心惶惶、需要逃避现实和宣泄情感有关,《僵尸先生》在1985年问世或许并不是巧合,《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的签署使得九七大限(1997年)将至的焦虑成为港人群体的普遍情结,此时港产电影往往具有星理压抑和自我开解的多面性,都或多或少与政治过渡的不安和矛盾有关。港人文化身份认同的普遍焦虑,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内在心理机制。已然入土多年的祖先尸首忽然无故重现、为害人间,正是一种对于国族历史身份的不自信。成长于七十年代的香港一代,对于父辈故土中华的集体意识缺少必要的感知和认同,《僵尸先生》中乡村首富为风水将入土为安父亲重新安葬,恰是一种重塑自我历史本源身份的隐喻,而重现人间的父辈变化成惊惧可怖的行尸走肉,并最终让子辈死于非命,则表现出港人对国族身份的一种象征性拒斥。
正是这种拒斥,使得僵尸喜剧投射出港人在国族认同层面的“撕裂感 ”。来源于明清停柩浮厝之 民俗,显现于清代志怪笔记小说的中国僵尸,却在香港影人的改造过程中具备辨识呼吸、吸食人血的西方吸血鬼(Vampire)气质 ,本身即是一种土洋结合、非中非西的产物。香港影人通过游戏仪式化叙事极力赋予这一形象合法性的努力,可归因于一种文化层面的身份自塑。
八十年代中后期,融合西方价值、中国传统乃至香港在地经验的港式文化,力图通过多种大众媒介达成其文化自足感,存在于僵尸喜剧中的茅山术(中国传统)与民初背景(西方价值)连同中西结合的港式吸血僵尸(在地经验)一齐完成影片制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这一共谋。然而,香港影人的努力虽造就港片十年的辉煌,却无法真正达成文化身份上的自在自为。杂糅东西方多种类型元素的僵尸喜剧,即便直接沿承功夫喜剧的类型规则,却无法像其经历沉寂后伺机卷土重来,而只能在本土与外埠文化的撕扯中走向分裂和迷失。这种撕裂的文化心态,恰若香港意图自塑之全球本土化城市形象最终却在文化认同迷失中变成「无法识别的城市」。
时代背景催生的港式吸血僵尸形象与「吸血僵尸喜剧」,正好弥补并缓解香港一代人在文化认同上空位缺失的焦虑情绪,在这层语境下的「吸血僵尸喜剧」的娱乐化刻板印象的再创作再塑造,就无法单纯从意识形态与文化景观角度展开批判,而是要顾虑到香港社会环境心态的矛盾性同步,位于中西两种文化认同感的居间地带不适宜感,恰好契合港式吸血僵尸形象的生死居间的暗喻,在两种文化互相交融消解后阵痛困惑期过后,试图妥协接纳呈现一副寻根不归根的主动姿态,建构只能存在于两方夹缝之中的「第三空间」,所谓的身份认同更广泛的可能性不在于那种稳固民族或文化认同,而在于一种矛盾迷茫中的「混杂式身份认同」。
(所以说,在芳香的黄符不小心掉落的情境之下,稍稍复苏记忆的方向站在红叶下时所吟诵和歌之时,存不存在这样的混杂式身份认同的矛盾性呢?)
 artworks/28681999
artworks/28681999话又说回来,港式吸血僵尸与「吸血僵尸喜剧」的文本叙事本就不止两岸三地的学者群体所涉猎研究,在「林穎汶」女士于2021年8月17号刊载在《京都大学映画メディア研究 1》上的研究论文《終焉と蘇生——「キョンシー」における表象の再構築》,文中观点着实较为新颖特此分享:作者认为在香港影坛九十年代吸血僵尸为代表的影片中,香港人熟悉的都市生活空间因1997年的即将到来,被刻意他者化的都市空间从而让幽灵、怪物、死亡、过去等概念所附身,使得电影中承担前现代价值观教化观念的「香港=家」的概念变化成极其不稳定的空间。特别是昔日七十年代的香港与旧式公共生活小区的怀旧记忆,在新式住宅小区普及变化得较为陌生,试图唤醒集体记忆中的小区邻居人情味的同时,给予观众既边缘化又熟悉化的氛围。
逐渐从外在的威胁转化成为内在的不安,相较于八十年代后半的「吸血僵尸喜剧」中刻意凸显前现代中国性的特指,九十年代的僵尸电影却大范围削减前现代中国性的特指联系,使僵尸成为恐怖的表象的并不是将来自外部他者或者怪物化,而是在家内部的丧失、剥削和暴力、欲望等成为产生僵尸怪物化的心理诱因。并高强度反应当时香港社会内部的现实问题,对共同体内部崩溃和丧失的强烈不安和危机感,自省与反权力是这一时期僵尸电影的核心命题。
(表述为九十年代香港的种种社会怪相均影射在其中,八十年代后半的「吸血僵尸喜剧」显然无法涵盖愈发复杂的僵尸片类型,这里僵尸肯定是脱离原本框架的创作性存在,好歹为僵尸和都市传说本身的契合性提供基础,虽然这文化景观是在日本人的他者视角中达成的。)
论及从现实中的日本人视角的「吸血僵尸」形象的话,可检索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怪异.妖怪数据库中检索「キョンシー」时所记载的传承文本,主要为「久野俊彦」博士于1999年3月20日所发表在《下野民俗 通卷39号》的民俗学论文《高校生が知っている不思議な話》当中记载到栃木县下野市的某所高校的高中男生群体间流行的都市传说,从属于学校场域内的都市传说文本:在小学生的时候曾经见过僵尸(小学生の時にキョンシーを見た)。
上述案例得以窥见,港台僵尸电影热潮作为日本本土不存在的完美异文化客体,而高校生群体又是作为输入方与接收方对其的刺激无疑是强大的,特别是僵尸电影中刻意不考虑现实道教要素的僵尸电影无不根植于高校生群体心中,从而形成某种本质娱乐化扭曲化,源于「古中国」的刻板印象叠加并脱嵌于现实道教层面的误解性「僵尸化」的表面形象文本,「僵尸化的僵尸」结合都市传说的在学校场域内的契合度更是如此。较为可惜的是,案例调查记载已经是1999年左右的事情,而在港台僵尸电影热潮褪去的当下,姑且不提泛ACG领域对于僵尸文本的认定为过时俗套的急速下降趋势,据IGN JAPAN编辑部的问卷调查当代日本年轻人对于僵尸的普遍认知度是有所下降的,相较于以往在港台僵尸片影响下围绕僵尸为主题所设计的角色,如今却更多是角色的皮肤与细节的要素设计蕴含认为是「僵尸」的古中国风的异域视角的简易捏他而已,而「宫古芳香」在当下大环境来说无疑还是更为正统化的僵尸片中的僵尸形象就是。
按照这层语境逻辑来看,往往千禧年之后,活跃于文本数据库中的「僵尸」并非是传统的二十八十年代后半的港台「吸血僵尸喜剧」的「吸血僵尸」,取而代之完全是后续经由文化间的认知差距脱离元语境并重新建构的「僵尸化」他者或某物,从始至终都是象征性模糊化「古中国」的异文化寄托对象的「僵尸化」,兴许正是在本文化语境中寻觅不到近似概念比对的日本人文化视角中的道士与僵尸甚至是纯粹僵尸形象的本质也说不定?
 twitter.com/yuuyuu_zenn/status/1044519106219663360
twitter.com/yuuyuu_zenn/status/1044519106219663360
总之,在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席卷全日本的僵尸热潮后,缺少不了后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泛ACG同人领域的僵尸文本化用,譬如ZUN在「神灵庙访谈」中提及的初期设定的宫古芳香形象与1995年3月卡普空发布的《ヴァンパイア ハンター Darkstalkers' Revenge》(简中翻译:《恶魔猎人 恶魔的复仇》)中的登场角色——「灵幻少女」レイレイ(本名少泪泪)的关系的话,ZUN眼中的少泪泪虽说具有僵尸属性的仙术师角色,内在却是干练的拳法家少女形象更为深刻,而且少泪泪身为拳法家僵尸的同时也存在负责通过符札操控她肉体的对象,即身为姐姐和智力担当的少铃铃。名字来源则是日语幽霊中的「霊」(レイ)读音重复两次而由来,原本这是开发阶段的初期命名而后续改动成读音相同的汉字「泪」就作为正式名称采用,在游戏本体中少泪泪的对战台词更是多以嘲讽为主,企划负责人则认为:“泪泪的背景故事很沉重,所以至少不想让他说出怨恨的台词”,如此多样的要素叠加变相增加泪泪的角色深度,时至今日,人气依旧不减当年。
较为巧合的是,少泪泪在游戏海外版的名称译名被变更为「Hsien-Ko」(何仙姑),系基于姐妹两人为拯救被黑暗俘获的少家母亲灵魂,姐妹俩人同时实施的少家禁术的「异形转身术」后,自愿沦为僵尸和黄符同黑暗势力战斗时,两者的正式化名称这一追加设定,更为有趣的是,系列游戏中登场的少铃铃多数时候是变化为贴在少泪泪的帽子上的有表情甚至能巨大化的黄符御札与泪泪一同参战的,同时防止泪泪随时失控而暴走进入「離猛魂」状态,而少铃铃的名称同样被变更为「Mei-Ling」或「Mai-Ling」(梅琳)。故事本身的话,姐妹俩人是为拯救因为保护自己而使用禁术消逝的母亲灵魂,但异形转身之术同样是「将术者灵魂变成永远无法拯救的灵魂之术」。临近游戏终盘结尾时,姐妹俩人虽成功拯救母亲灵魂,但生命火焰却消逝,在俩人战斗中被净化拯救的母亲灵魂,在表达感谢的同时让女儿们作为新生命而转生。
在游戏本体中作为格斗机体的特点是机动性普遍低,但通常技能与特殊技能的输出范围相当广,且必杀技相当独特,浮空释放技能判定点过大,往往处于不利的位置。机体本身的连招释放情况配合较为复杂,压根不存在无敌对空技与防御取消的功能,并不是适合防守向慢慢磨血条的角色。在后续系列游戏当中,同样是高强度吃玩家本身操作的角色,通常是面向格斗游戏上级者的较弱角色,但在近身格斗部分非常强,可以说相当契合僵尸的特征。不知道ZUN在设计芳香符卡时是否参考过少泪泪的机体特征呢?泪泪的特殊技能和芳香特色的HP回复符卡没什么实质上的借鉴,但在泪泪的游戏立绘中最引人注目的潜藏在宽大袖子中的六根勾爪和暗器,多少还是和芳香的「毒爪系」符卡存在一定的关联,好歹在MUGEN里面客串登场过。
(或许正是「少泪泪」的背景故事在同年代的格斗游戏中较为沉重的内因,毕竟少泪泪作为格斗游戏主角却在当年被玩家评价到「从未见到身世如此悲惨的格斗主角」;加之在《东方神灵庙》的构思阶段所处年代的泛ACG化的僵尸少女形象过于俗套的缘故,最终促使ZUN将按照泪泪形象为灵感设计的初期芳香改动成脑子烂掉的现版本芳香,果然悲惨背景的僵尸系角色还是受欢迎的?就是不知道泪泪擅长拳术的格斗原型,是否是对《茅山僵尸拳》的再创作?)


本章节的最后,结合去年的空间动态,谈谈芳香头上黄符符箓的原型,要注意到几乎不少道教符箓前缀几乎都会有“勅令”这两字,勅令即为道士们篆写的符咒,结构上来说:勅、令、之要连笔书写,而中间像绳结的部分是“之”字的尾巴,要固定转三次而不是两次。另外,勅/敕/勒三个字要分清,读音chi/chi/le,都是第四声。勅令是一种强制驱魔命令,一般都是道士使用来对阴兵发令;敕令多为皇帝的命令,当然帝王也可以用“勅”令,勅本身由束和力构成,勒令是指用命令的方式差遣他人,普通人也可以用。一般来说,「勅」为「敕」之异体,亦有以这两个字来区分皇家的「敕命」与道术的「勅命」的说法在。符箓在茅山教中亦称“符字”、“墨箓”、“丹书”等,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称。符指书写于黄色宣纸、帛上的一种图形的符号、图形;即是道士把一些道教咒律以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箓指记录于诸符间的天神名讳秘文,一般也书写于黄色纸、帛上。道教声称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驱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
芳香头上的贴的符箓,到底写什么?据ZUN的神灵庙访谈,基本可以认为系港台「吸血僵尸喜剧」片中同款的“随身保命符”或者“大将军到此符”,虽说都是电影中捏造虚构的“镇尸符”与“僵定符”。前者随身保命符多用于电影中虚构的茅山道士使役僵尸时的黄符,强调某种使役操控的氛围;而后者的大将军到此符中的大将军指涉对象存在白乙大将军/白乙丙或者钟馗的说法,实质上就是附会某位统率怪异的武力化对象,更加强调其镇压尸身的属性,毕竟只有异动的尸身才需要符镇来停滞行动,而现实中的南传法教内部也不存在如此被艺术化夸张加工后的派系就是。
兴许是怕引起什么谬误,ZUN几乎在官方作品芳香出场的时候,都只展示了符箓上的“勅命”两字。但在《人妖名鉴.宵暗篇》当中,shnva老师倒是根据自己的想法,给此前一直留白的符箓补充了点内容,笔者对比之后警觉此符箓非常有着茅山教的味道,可惜实在过于模糊,但芳香头上贴的是属于茅山教的符箓这点基本没跑,其余南传法教或南巫派系道教的闾山教、梅山教的符箓便是以实用性著称的,有点地方甚至直接画出符箓代表物顶上去的,相对来说茅山教这支有着法术源流回溯崇拜的派系还算成熟,主要就是看茅山教符箓的特征。
要是涉及现实原型的话,个人猜想应是如上图比对角度,茅山教中道士使役豢养阴兵兵马的「镇煞召鬼符」,芳香即为贵为邪仙的青娥,依照南传法教中茅山六壬的刻板印象设计的茅山道士所使役的兵马就养兵马、炼兵马这点,可以说芳香即为青娥娘娘使役豢养的「阴兵兵马」,早就已是笔者的老观点,建议联动重制版的青娥专栏配合参考观看。
川蜀道门元皇业内人士的看法:正经道教派系的僵尸,其实大多没那么玄乎,都是开棺直接用经年使用的特制斧子砍头, 搞不定的上鸟枪,不然直接跑,在僵尸头被砍下来之后一般都是黄符封印复合钉封入罐禁内钉灭其灵体,好处理的就是用来使役「养兵马」或者「运阴兵」,难处理封入尸棺内之后,淋上桐油直接烧掉。
 artworks/55800785
artworks/55800785
其二 民间志怪文学「尸变型僵尸」的文本嬗变和变迁
就在ピクシブ百科事典的宫古芳香角色词条的备考条目中,条目编纂者在游戏整作对话和《东方香霖堂》查阅检索过「僵尸」本就存在于幻想乡的结论:僵尸似乎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幻想乡,不仅是在外面世界看到创作物知道僵尸存在的早苗,魔理沙、妖梦也知道僵尸是什么的样子。森近霖之助在葬礼的话题时进行考察:“在幻想乡,人类遗体是土葬的,所以遗体死后有可能变成僵尸和吸血鬼。最近,人类供养从土葬切换到火葬,所以变成僵尸的遗体会减少吧。”留下强烈留恋而死去的人和被术士施术的尸体在死后苏醒成为僵尸。芳香被认为是后者,本人似乎没有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由此可得,幻想乡中的僵尸与丧尸概念或许就较为模糊化且混同?就从阿燐符卡的化妆成丧尸的妖精形象,不同于芳香所代表的幻想乡僵尸形象,可能幻想乡中存在僵尸的具体设定起码要在神灵庙时期最终完善,否则就只是存在于台词与对话中的一种妖怪化概念,《香霖堂》倒是提到僵尸与吸血鬼重要成因的「尸变」型叙事,源于传统丧葬仪式风俗的遗体的二次转化,且认为最近幻想乡火葬普及使得土葬风俗空间被挤压,遗体转化成僵尸与吸血鬼的案例会减少,而土葬风俗的遗体转化成的「尸变型僵尸」和邪仙术士使役的「吸血型僵尸」(只有青娥与芳香)的两种概念在幻想乡中同时是存在的,使得在ZUN的设计中巧妙地融合到一起,总之两种方式转化而来的皆为僵尸就是。
倘若重新溯源「僵尸」的词源词义到底为何物?首先,在古代文学中的「僵尸」确实不是一个陌生概念,但因僵尸一词实在过于含糊。从广义语境上讲,僵尸是极为平常的东西,只要人死血液凝固就会遗体僵硬成为「僵尸」,通常为古代文学典籍中记载的战乱或者饥荒年代的文字「死者不可胜数,僵尸遍野」、「僵尸如麻,人相食」,「僵尸」早期词义在历史文献私聊语境的指代多为此类。且因「僵尸」指代描述的对象往往是针对遗体本身,自然在后世文本变迁中的「僵尸」词义逐渐泛化为遗体体表的异象变化,乃至于延伸至传统丧葬礼俗的遗体转化的社会规训臆想,传统封建社会环境在对待死亡的礼俗越是发展,越是将遗体相关的民俗仪式视为不可逾越的心理性障碍,凸显出社会环境面对死者遗体的态度变迁,在社会内部潜移默化地形成关于死者遗体的禁忌,「僵尸」的词义泛化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如果从角色设计时参考的原型文本诞生年代来论证,芳香系经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的港式「吸血僵尸」概念,再诠释再创作再化用的角色设计本身无疑是幻想乡众角色中最为年轻的一批?顾虑到港式「吸血僵尸」成型系借由西方吸血鬼题材本土化的设想,均取材自清末志怪小说文学的「尸变型僵尸」文本的话,原型文本上完全同步于青娥原典出处的《聊斋志异》时代背景好些,而无论如何青娥芳香这对「南传法教茅山道士与僵尸」的标准图样,的确是同时期的清末志怪文学建构生造而成的印象,且几乎不存于任何历史文献史料语境当中,反而是只存在民俗语境志怪文学小说的产物。

据海力波教授所撰发表于2012年第2期《民俗研究》上的论文《生死问的暧昧:清代“尸变"故事中的观念与情感》:清代志怪小说中多收录「尸变」故事,此类型故事往往以死者遗体不腐或发生变异为祟人间为主要内容,即民间所谓的僵尸或诈尸害人的故事。「尸变」故事影响甚广,不仅在清代与民国通俗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成为现当代的影视与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尸变」故事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李肃《纪闻》“李虞”条记“全节李虞好犬马,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田猎焉。”段成式《酉阳杂俎》“河北村正”条记“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至,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入墓林,约五六里,树下有火莹莹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而还。”这两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尸变」故事,故事中死者并未复活,未幻化为无形的鬼魂,而是尸体本身发生某种神秘、不 可解释的变异,成为某种介于有形之人与无形之鬼之间的存在物。
宋代,「尸变」故事内容更为丰富,洪迈《夷坚甲志》“嵊县山庵”条与“张夫人”条所记「尸变情节更为具体曲折,“嵊县山庵”中死者尸体可模仿生者的行为,追逐生者。最后“跄踉直前,抱一柱不舍,抱柱牢不可脱”;“张夫人”中“至半夜,尸忽长叹,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呀然一夜叉也。”这些细节描写,在以后的「尸变」故事中反复出现,成为此类故事中的典型情节。宋代「尸变」故事中的僵尸已经会作祟害人,明代则更将僵尸视为给社会带来灾难混乱的根源,认为葬而不腐的尸体会变化为导致旱灾的妖神旱魃,因此在民间普遍流行发冢焚尸的打旱魃习俗。
清代「尸变」故事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叙述模式,大致分为“触犯禁忌”型与“妖魔害人”型两类,亦如纪昀所云:“僵尸有二,其一新死未敛者,忽跃起博人;其一久葬不腐者,变形如魑魅”。袁枚《子不语》卷八所记「尸变」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同名故事都是“触犯禁忌”型的「尸变」故事的代表之作。在清代志怪文学中「尸变型僵尸」文本多以“妖魔害人”型为主,僵尸大多似人非人,介于人、鬼之间,为祟人间,甚至具有神通,能够决人生死。清代志怪小说中的「尸变」故事虽为文人之作,但文中往往言明从何地、何人口中听闻转载,虽可能为作者所假托,但也极有可能是以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为蓝本润色加工而成。在今人看来,僵尸为祟之事固然不足为信,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此类观念的确存在。诸如防止猫狗不能跃过逝者的灵柩,活人不能与死者对足而眠,以防猫狗和生者的阳气贯注死者足中,引起走尸的禁忌,「尸变」故事具备深厚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土壤,更有可能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不能视为单纯的文人创作。
「尸变型僵尸」介于古人所相信的人鬼阴阳世界的边界间,而引发「尸变」的原因主要是人们打破阴阳人鬼世界中的时空与伦理秩序所致,生死秩序的混乱才是「尸变」的主要原因。秩序的混乱有可能是单纯的时空秩序的打破,也有可能是伦理与道德秩序的失序。多数「尸变型僵尸」文本均有生人路过荒村、古寺、废宅、旧冢、山林野店等地,从而引发尸变转化为僵尸生人受到袭击,便是揭示这一道理的写照。对他人空间的擅入,隐含着对他人身体和自尊的睥睨、窥探和侵犯,不何尝也是人对鬼界的一种主动进犯呢?无论是触犯禁忌型或是妖魔害人型「尸变」故事,皆寓意对时空秩序和其背后的伦理道德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正是这种对秩序破坏才导致「尸变」的发生。正因为「尸变」的原因通常是由于非礼、逾礼的行为所致,镇压僵尸之法,通常是在象征意义上将被打破的秩序加以恢复。
(关于这点,请各位自行观看港式「吸血僵尸」电影中用以退治镇压僵尸道具就明白,道具属性本身无一例外具有划分人鬼之间区间界限的规矩含义,从变异之中寻求对于常态的回归。)
借由「尸变」而深入到丧葬风俗层面的话,清代「尸变型僵尸」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就在于宋至明清时期风水堪舆说对民间丧葬风俗带来的巨大影响,作者结合清代中后期「尸变型僵尸」文本的志怪小说作者们的创作思路与出身地,认为人们在为讲究风水堪舆而令逝者停柩浮厝和令逝者尽快入土为安这两种观念与习俗间的拉锯纠结和心理冲突,正是引发古人对生死秩序被破坏的「集体无意识」忧虑的原因。为求风水吉地,人们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先人故去后,因找不到「吉穴」而将灵柩停棺待葬,成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清代社会的独特葬俗,时人称之为「停柩浮厝」。「停柩浮厝」之俗在地域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大江南北皆有,尤以安徽、福建、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为盛,其中更以江南地区为最,清代江南地区「累世浅土,十室而五」「尘积于堂中者十家五六」,「停柩浮厝」之俗令逝者与活人并存于同一生活空间,死者棺柩乃至尸骸经常性地曝露在人们的视野中,甚至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相糅杂在一起,成为清代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特殊的社会景观。
(以笔者亲身经历举例的话,个人在徽州至浙北一带古村落进行明清徽派古建筑文旅之时,曾经在当地古村落某些弃之不用的清代老宅中见到放置在偏房或侧天井中的半遮半掩的空棺材,应视为清代江南地区停柩浮厝的民俗行为的衍生迷信文本。)
因此,在当时官府和民间视野下,停柩浮厝葬俗是一种“似葬非葬”的习俗,人们难以确定此状态下的尸体是否可视为已经被葬埋,令逝者在活人视野中处于某种尴尬暧昧、身份不明的地位。正处于葬与曝之间的过渡状态,违反了人居于阳间地上、鬼居于黄泉地下的原则,停柩浮 厝之俗不仅使逝者的尸骸被不当曝露,更令逝者的身份产生某种暧昧的性质。在清代尸变故事中,导致僵尸作祟的直接原因,往往是逝者得不到合适安葬、停柩浮厝、未能入土为安所致。
再从流传地域上来看,虽然各志怪小说集中讲到在清代南北各地都有尸变故事和相关禁忌与信仰,但对尸变故事记载最多的仍然是江南文人的作品,作品中尸变故事的发生地也多在这些作者所生活的江南地区;诸如袁枚是浙江钱塘(杭州)人,俞樾是浙江湖州德清县人,许奉恩为 安徽桐城人,王韬为江苏苏州人,其所生活的地域大致在江南一带,生活的时代也都在清中后期。在时间与流传的地域范围上,尸变故事与停柩浮厝的葬俗大致上可重合。
清时风水堪舆观念的盛行导致停柩浮厝现象的普遍存在,视为尸变故事得以产生流传的社会与时代背景当无疑义。而停柩浮厝令逝者尸骸曝露在生人的日常空间中,令生者对逝者产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度,同时给生者带来心理压力和恐惧、厌恶之感,也是尸变故事中得以产生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背景。
上述论文提及的两则唐志怪「尸变型僵尸」文本,均有生人访之墓林扰乱场域的情节存在,而清代「尸变型僵尸」的志怪文学小说则承袭前者,生人不小心闯入僵尸场域空间内的入侵行为与僵尸行动并被动防御的暗示,既然生人/外来者打破物理层面的时空秩序与心理层面的伦理秩序,以僵尸的方式激起面对外来不速之客的抗暴行为,元文本中呈现出的完全是死者冤魂抗议与报复的独特方式,「尸变型僵尸」正是这一故事文本中孤愤与寄托心理转化的表征。

客且奔且号,村中人无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门,又恐迟为所及。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至东郊,瞥见兰若,闻木鱼声,乃急挝山门。道人讶其非常,又不即纳。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障;彼右则左之,彼左则右之 。尸益怒,然各浸倦矣。尸顿立。客汗促气逆,庇树间。尸暴起,伸两臂隔树探扑之。客惊仆,尸捉之不得,抱树而僵。道人窃听良久,无声,始渐之。见客卧地上,烛之死,然心下丝丝有动气。负入,终夜始苏,饮以汤水而问之,客具以状对。时晨钟已尽,晓色迷津,道人觇树上,果见僵女。大骇,报邑宰,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聊斋志异》卷一《尸变》
简单援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段宗社」老师发表在2008年的《聊斋志异研究》上的文学论文——《论「聊斋志异-尸变」、「喷水」的寓意》:《尸变》中同样呈现即陌生的入侵者对私人空间的侵犯这点,从而引发女性遗体的尸变反抗驱赶自己空间场域之内的入侵者,叙事本身天然具有某种文本的评价残缺感,说白了就是在文本中无法呈现僵尸对象作恶的缘由,旅者和女尸完全是萍路相逢的关系。在这段叙述中,蒲翁完全按生人的情态写女尸,她成死而复生的生命体她有生人的体力,有体力消耗而來的困倦和喘息。最后「抱树而僵」则因耗尽体力,按照世俗生命世界的逻辑渲染拼死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场面,似乎有意要营造出某种深仇大恨的体验,事实也确实如此,只是不能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待。需要补充的是,《聊斋志异》通行本的篇目排序并不能反映创作时间的早晚,《尸变》其未必属于早期创作。
《尸变》中由店主人所导引的入侵事件更为严重。「子妇新死」,这家却无丝毫悲戚之意。小店生意如常,并且「客宿邸满」。没有按照礼俗搭建灵堂祭奠 ,只是匆匆停尸于死者原来的房间,小丈夫被派出去采购棺木,灵前只有昏黄的烛光守候 ,应有的纸钱祭奠一概阙如。尸骨未寒,有人便带领四位远路客商占据亡妇的床榻,概由怨愤所致,一语道破尸变之缘由。
《尸变》中客人匆忙中所投奔的破庙被刻意改写成一座完整的兰若,围墙高耸,木鱼之声可闻,而山门紧闭,虽急挝(敲击)山门,但道人讶其非常,又不即纳。道人是庙宇主人,有权接纳或拒绝任何外来者。就是说 ,道士拥有对兰若的处置权,夜半时分,有权对敲门者置之不理。这细节实则为我们提供入侵与防御的暗示,是金圣叹所谓「背面敷粉法」:以道士可以以将外来者拒之门外,暗示亡妇没有一扇大门可以抵挡入侵者。作者以深夜道人闭门念经的细节突出亡妇之无力捍卫私人领地的窘境。故事表面上所残缺的起因,实际上已经在作者精妙的叙述中作深藏不露的政治性暗示,及反抗入侵者的政治寓意。
又据「李丽丹」博士于2016年所撰《耿村与「聊斋志异」同型鬼故事比较研究》: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将此类故事定型为「114、死鬼追踪」: 一个男人夜里碰上了一个死鬼,他逃了—— 死鬼追踪他——最后一瞬间男人得救。艾伯华共搜集十一个文本的异文,其中包括《聊斋志异》,在补充母题(1)中,艾伯华指出「通常是几个男人,死鬼通过闻的办法杀死所有的人,只剩下一个」,这类母题在江苏等地出现,补充母题(3)中,表示在江苏、河北等地流传的这一故事类型中都是「僵尸用手紧紧抠进树里」,他在附注中指出「通过闻(夺走呼吸)杀人的死鬼追踪母题已经出现在袁枚笔下:《子不语》浙江等地,然而蒲松龄《聊斋志异》早于《子不语》的问世,且《尸变》为其卷一中的文本,当属蒲松龄前中期的创作,即最晚在十七世纪中后期,这类型母题就已经在北方(山东)地区流传,并被蒲松龄记录下来。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尸变》系据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谈氏笔乘》和清初至清中期「东轩主人」辑撰的《述异记》中的「僵尸鬼」形象再创作而来,或许存在某类明清交际之时肆虐山东等地的战乱流离的某种共同集体记忆?毕竟尸体各类异象对于这段特定时期的山东等地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转念一想,芳香还真就适合出没在《东方神灵庙》的本篇故事中,港式「吸血僵尸」中所参考的清代志怪小说文学的「尸变型僵尸」均有涉及到,二创同人图中芳香保卫灵庙向的创作一向不少见,芳香正是幻想乡与神灵庙之间的划分规矩所使役的对象,何况太子等人刚醒来时的梦殿大祀庙正好在命莲寺墓地之下,梦殿大祀庙的大门恰好又是「尸变型僵尸」的出没场域,相当之契合。)

相较于《聊斋志异》为对象的「尸变型僵尸」文本分界线的清末志怪小说文学,在这之后的涉及僵尸的清末志怪小说文学又是产生何种变化,以至于能成为本文第一章节中提及港式「吸血僵尸」的创作参考原型?笔者认为,莫过于僵尸文本相互之间的互文性、创作性,姑且需跳脱出大陆学者视角援引早稻田大学的中国诗文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者「中野清」老师于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中国詩文論叢》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笔者挑选较为重要的一篇,如《子不語の僵尸说話の創作性》一篇中:认为「尸变型僵尸」在《子不语》前的诸多清末志怪小说,并非均是以过于凶恶无比的文字描述形象为主,而是多以僵尸行动的故事情节为特征引人入胜,而《子不语》存在作者袁枚「性灵说」的创作特点,往往在故事文本前期埋下伏笔和双线并行,产生更为现实的恐怖故事结构。
论文作者列出探讨《子不语》的「尸变型僵尸」文本中未加工抄写的案例:《僵尸手执元宝》宛如雍正九年山西地方灾事的传闻被记载下来,没有增添撰写任何多余的文本加工,基本就是山西商人间口口相传的事实,无非是地震后被埋没的尸体手中抱着金元宝的轶闻。
文本经过少量加工的案例:《牛僵尸》牛本牲畜,老弱不能为人所用,本当宰杀取食,但主人因为对其感情深厚,而将其视如人类,待其死后加以掩埋安葬,视畜为人,同样是一种非礼的行为,反而引发牛变为僵尸作祟,如果存在加工痕迹的话,即为针对元文本加工为牛僵尸生前为主人家诞下二十八头牛的数量上的夸大化和牛僵尸大闹农田的情境。
几乎会在故事传播时就被记述下来的案例:《飞僵》完全是身为袁枚好友的颍州蒋太守,对于某位手已不听使唤的老人武勇传的阐述,袁枚则几乎原封不动地全部记录下来的文本,故事更是采用老人为对象的一人独白体来展开故事,讲述为当地居民请命以自己为诱饵戴铃铛引诱吃小孩的飞僵,进入道士设计的圈套,从而退治拥有广大神通的飞僵的故事。
完全自我创作案例/创作之外无法想象的案例:《僵尸求食》/《僵尸贪财受累》或者《两僵尸野合》,具体情节在此不多赘述,这些袁枚自我创作的文本当中,僵尸形象在文本中变化得更有具人性,而受到生前未完成的各种欲望驱使的僵尸们,分别为食欲、钱财欲、性欲等原初目的而展开行动,面对僵尸作恶的心理描写方面更为细致,僵尸形象更是远没有前者《飞僵》那么凶恶。
(被各种欲望驱动的僵尸复合道士退治僵尸等要素,实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神灵庙。)
目前为此,关于袁枚《子不语》所开创的僵尸修炼系统/神魔僵尸体系文本系统又是如何来的?目前较多看法认为是袁枚的「性灵说」展开创作思路,面对上述案例的收集、堆砌各地域「尸变型僵尸」文本的再创作过程,结合唐人志怪文学的宗教色彩与清末民间志怪小说前人奠定的「尸变型僵尸」形象,不断堆砌混同创作形成的「神魔僵尸」体系,比如简中网络各大营销号特别爱用的「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及「魃、犼」等概念。均可认为,袁枚笔下「僵尸」设定即为历代志怪小说和民间迷信延伸和牵强附会的表征。

话说回来,提及清末志怪文学小说的「尸变型僵尸」和「神魔僵尸」体系的文本嬗变的话,民国初年的民间戏曲领域是个着眼点,各类活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的上海戏曲界较受欢迎的「民国僵尸戏」,可能蕴含当年张勋复辟北京城内部辫子军的四处找清朝服饰穿戴的集体记忆影响?但二者均在客观层面上推波助澜地传播不同于聊斋「尸变型僵尸」和袁枚「神魔僵尸」的「新式世俗化僵尸」设定。何况存在长期被认为港式「吸血僵尸」设定原型而生造出来的刻板印象——「湘西赶尸术与赶尸匠人」,作为民国初年被神秘化的湘西地域的象征,同时代的民间志怪小说中则沦为「神魔僵尸」和「民国僵尸戏」的文本原型去传颂的刻板印象文本,一开始就作为神秘化文本原型被传颂的「湘西赶尸术」民俗文本。
这要归功于以《清稗类钞》(主要记述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期的稗官野史)为代表的民国初年志怪小说,在袁枚草创的「神魔僵尸」体系上,加大力度混淆道士与僵尸、道教与僵尸的刻板印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湘西赶尸术」,本质上系某种「乡土他者化」的表征,造就目前互联网语境在讨论「湘西赶尸术」话题时的窘境。准确来说,「湘西赶尸术」的真实概况应当视为:刻板印象混淆造就的「乡土他者化」的「湘西赶尸术」,以及可以存在的却不被湘西苗族群体称为「赶尸术」的苗族风俗,而苗族巫师和道教道士在历史语境中的确发生过至少两次大交融。
根据担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的「麻勇斌」先生于2017年所撰一文《苗族民间异术简史:生成与演变》的观点:在外界关于苗族民间异术的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术类,就是所谓的“放蛊”和“赶尸”。所以,从帮助外界了解苗族之巫的角度出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必须说明清楚这两种术类。一是,“赶尸”活动可能存在,在民间称作“赶尸”的术类,苗语没有称谓,但可以肯定,“赶尸”活动,在苗族历史上是有的。“赶尸”在苗族历史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苗族至今还有招亡的习俗。苗族人笃信生命永恒。所以,苗人“事死如事生”,解决冲突的公理是“死的为大,伤的为忧”。一旦遇到丧亡,尤其是意外丧亡,举家、举族、举寨同悲,必相互帮助,不惧千难万险,也要找到尸骨,找到死者遗物,予以礼待,隆重送别。所以,在外作战阵亡、谋生遇到不测,其家人族人都会竭尽全力把尸骨找回。这样,就催生帮助丧亡者找回尸骨的行当。由于苗族社会长期存在这种需求,找回在外丧亡之人的尸骸、给予礼待,就成了苗族之巫的重要服务项目,被后世之人描述成“赶尸”的找回和礼待在外丧亡者的“巫”与“术”就应需而生。
二是,“赶尸”活动的隐秘性可能是生存环境所致,明清时期,苗族与中原皇家多是处于敌对状态(贯穿明代中后期至清中前期的赶苗拓业运动),战争频繁发生,意外丧亡、流落深山的人太多,找回亡人尸骸的工作必然非常繁重和迫切,而且,这些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才能避免惊动官军,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被后世之人称作“赶尸”的寻找丧亡者尸骸的活动,都在夜晚走路。由于寻找亡人尸骸这个行当不仅需要胆识过人,而且需要杀鬼驱邪的本领,苗族之巫与道教才在此形成了完全融合的术类。所以,具有镇邪驱鬼功能的神秘符咒,就充斥了整个运输尸体返程的过程; 具有苗族生命哲学思想的法门,贯彻整个运输尸体和处理尸体的始终,比如,尸体的手脚必须束紧,并裹上一层杉木皮,然后绑定在两根与之齐高的木棒,使背负尸体的人与尸体处于背对背的状态,这样,尸体返家的过程始终是后退的方式。休息时,尸体始终是能够站着的。如果尸体过多,或是返程的路途遥远,则只取其头和战甲或衣服返程。“赶尸”必须有“文武两教”的师傅。通常,“武教”师傅在前开路,“文教”师傅在后消弭踪迹,背尸体的术士走在中间,所有人必须倒着穿鞋。寻找丧亡者,安顿丧亡者,是活人对死人尽情谊、寄哀思的过程。其中的法术,无非是应对和防止死人由于无知、怨恨而伤害活人,应对和防止在过程中遭到敌人、猛兽、鬼魅的袭扰,而生成的技巧和方法。在这些法术里面,既有苗族之巫的术类法门,也有道教术类法门,还有佛教术类法门,应证了“万法归宗,万法归理”的同时,透露出苗族历史的一幅惨景,和苗族在极其艰难的明清时期,同胞之间生死不弃的令鬼哭神泣的情义。
同样的,在日本関西学院大学的「李軒羽」研究员发表于《関西学院大学先端社会研究所紀要》2022年3月21号的纪要论文《中国における現代説話の伝承動態:湖南省ミャオ族の事例》存在近似观点:用中国古文书数据库进行检索调查的结果,可以说在清代之前,不存在直接指出「赶尸」的记述。因此,相关案例主要引用于清朝稗史(民间编撰的非正式史书)和近代随笔。据民国时期的记载,赶尸过程更加明确(老练地进行念咒时的禁忌,甚至提到手势),这些都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赶尸传说的典型创作模式。此外,沈从文的随笔集中还留下这样的记述:湖南省沅陵县有机会目睹赶尸现场,多名死者排队行走、靠近汽车时尽量避开、死者被「辰州符」操纵等要素。
一部分先行研究指出清末「尸变型僵尸」-「神魔僵尸」传承的流行和「湘西赶尸术」传承文本的关系。尽管清末僵尸传说较为流行,却并没有发现与「湘西赶尸术」相结合的记述,两者的因果关系至今不明。且在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赶尸目击谈的传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港式「吸血僵尸」对于「湘西赶尸术」文本刻板印象的再成型,特别是1990年以来,演员经常以苗族民族服装的姿态登场,湘西地区被选为外景拍摄地。时至今日的「湘西赶尸术」早就是不知道再塑造过几次刻板印象的文本,但无害化消弭掉原本带有他者化歧视的要素,仅是作为宣传湘西地域的旅游资源被宣传。
归根到底,「湘西赶尸术」作为某种具有乡土他者化与猎奇性质的文本在清末民初作为文本被传颂传播,并入「尸变型僵尸」-「神魔僵尸」-「民国僵尸戏」-港式「吸血僵尸」这一长串的发展变迁关系中,而原本真正属于湘西苗族地域苗巫道士群体的「运送客死他乡的苗人尸体」的这一项技术,并入大众印象的僵尸体系之一的「湘西赶尸术」文本,无论如何发展倒始终和苗巫们的技术牵扯不上关系,仅仅是作为苗族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生产生活中逐渐生成的民俗行为,至于港式「吸血僵尸」形象与刻板印象的「湘西赶尸术」恰好是阴差阳错、牵强附会的大闹剧而已。
 artworks/19800521
artworks/19800521
其三 「亡者归来/活着的尸体」型的跨文化叙事
总而言之,虽在本文前两章节的笔者在试图强调僵尸文本的非混同的独立性,展开现代民俗学角度视野下的「吸血鬼」和「丧尸」及上文解析「尸变型僵尸」-港式「吸血僵尸」文本,在现代民俗学常用母题分类法的AT体系中系从属同一分野的「亡者归来/活着的尸体」型母题。三者间在各自文本发展的早期均是并非死者苏生型母题的,介于生死界限间的存在,毫无疑问是具有各自叙事背景的母题互文性,通常表述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的早期土葬风俗背景,演变成对掘坟刨尸的焦虑恐惧的具现化。
准确来说,香港民众「集体宿命意识」的焦虑化产物——港式「吸血僵尸」,虽是西方吸血鬼题材的本土化产物,电影形象的认知内核却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是反应传统民俗教化价值观的喜剧娱乐化的港式「吸血僵尸」片的前现代性,喜剧中夹杂说教感是港式「吸血僵尸」片完全不变化的重要特征——模糊化的吸血僵尸,相反的是在自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吸血鬼」文本中关于宗教和阶级的描述一直被弱化,当代吸血鬼角色不再像过往传统吸血鬼形象高高在上,再结合美式吸血鬼题材电影的多元现代化的复杂精神倾向——容纳社会诉求题材的万能框架对象;同时需要注意针对社会现实批判的丧尸电影的后现代性——绝对他者化的政治性异化肉体。三者在当代电影题材中的形象呈现,又恰好影射三种不同的心理意象。
按《电影中的僵尸文化》研究美式丧尸形象的论文集摘录的文段观点:书中提到,僵尸最初诞生于海地的伏都教中,通过魔法将死去的人复活,成为介于活着和死去之间的生物,没有意识的奴隶,并且渴望活人的血肉。这就是僵尸最初的雏形,僵尸的英文“Zombie”,也正是出自海地语。僵尸最早依然多数存在于文本书籍的层面,这时候的僵尸形象还没有固化。在被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僵尸文化的起源——民俗传说中,提到僵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心灵僵尸,另一类是已经进入流行文化类型中,由死者复生的身体转化的物理僵尸。显而易见,这两类僵尸里,心灵僵尸的战斗力强于物理僵尸。区分这两类僵尸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心灵僵尸是没有身体的灵魂,而物理僵尸是没有灵魂的身体。
最初的僵尸,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样行动迅速,吸食人血人肉,而是身体憔悴,行动缓慢。而僵尸食人这一设定,则是把僵尸与另一种食尸鬼(ghoul)相混淆的结果,所以才有僵尸食人这一概念。实际上,僵尸形象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逐渐地成为丧尸形象,只是英语中对“僵尸”和“丧尸”不做区分,都用“Zombie”一词表示。因此书中所提及的僵尸有一部分实则是丧尸。僵尸与吸血鬼的不同主要在于二者所指认的身份,僵尸是地位低下的代表,而吸血鬼则是身份高贵的。僵尸文化的流行,其实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现象,书中的论文作者,已经将这一文化符号进行了某种学术的具象化,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变种,荧幕上的很多僵尸电影,其中的某种内核都是一致的。
在四川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余家良」研究员于2018年6月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丧尸电影研究》中认为:丧尸电影与僵尸电影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丧尸与僵尸的电影形象区分之上,通过笔者对现有文献的参考,以及对相关影视文本的总结发现,丧尸与僵尸的形象区别如下: 第一点,丧尸形成的源头是活人或者死尸因为某种药剂、辐射、异物入侵人体导致其转变而成;而僵尸形成源头是基于中国湘西赶尸和道教文本背景之下,死人由于生前冤屈,或者墓地风水阴阳失衡产生尸变而成。第二点,丧尸行动全部依靠本能步行、无法被人控制;而僵尸则拥有自主意识跳跃而行,会找生前的仇人复仇,并且可以被道士用符咒控制。第三点,丧尸掠食新鲜生肉,而僵尸只吸血。第四点,丧尸肢体腐烂、不怕阳光、只能通过爆头杀死;而僵尸身体不腐,怕阳光、只有桃木剑和符才能将其摧毁。第五点:活人被丧尸抓咬后无药可解,无法康复;活人被僵尸抓咬后可通过糯米拔毒等方式,逐渐康复。第六点:丧尸主要聚集成群体行动;僵尸主要单独行动。 通过以上对比,“丧尸”与“僵尸”是在电影中所展现的形象截然不同,是差别巨大的两个概念。
(那么,为何ZUN会在神灵庙设定文档中认为经由港式「吸血僵尸」形象设计而成的「虽然她其实和丧尸差不多」(ゾンビだけど)呢?或许是怕幻想乡现已登场的吸血鬼与吸血僵尸冲突的副产物,索性把丧尸概念合并一类项,毕竟另外设计个符合大众印象中的丧尸实在过于俗套,看上去差不多但却不是一回事,想表达的说不定正是如此?)
 artworks/52809373
artworks/52809373为何世界各地的亡者对象,皆会选择从墓地中归来生前之地呢?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叙事系建立在世界各地的初民们认为尸体腐烂前,灵魂作为逝者的主体会留在逝者肉体表示的客体之中,全面建构在肉体—灵魂二元论的基础,保持介于生死居间的阈限地带他者化对象的臆想。于是乎,世界各地在逝者丧葬仪式后的守夜民俗行为盛行,防止逝者在丧葬仪式出现任何意外的朴素情感。
另外,在东南大学医学人文系的「程国斌」博士于2018年冬季的《文化研究》期刊上的所撰的论文《乡关何处?——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灵魂与遗体处置的观念》:丧葬仪式,据象征人类学范热内普的经典定义,是死者「从一个境地到另一个境地,从一个到另一个(宇宙或社会)世界之过渡仪式过程」。仪式的顺利完成对于死者、生者及其社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徐烺光表述为:举行葬礼是亲属们对亡人应尽的义务,是家族平安,人丁兴旺的保障,是亲朋好友沟通关系的桥梁,也是显示家族社会地位的有效方法。葬礼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死者的灵魂去灵魂世界的途中一路平安,保证灵魂在灵魂世界安然无恙。两种功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民间有关鬼神的想象和信仰,即格尔兹所说的,在大众民间信仰中存在的有关何谓 “真正真实”的概念(不论如何模糊),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 “合理观念、实践观念、仁爱观念及道德观念”。
尸骸可以是完整的身体、经过处置的骸骨、骨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是经过招魂仪式之后附着了灵魂的象征物。坟墓借助尸骸成为阴阳两界相重叠的独特空间:一方面亡灵通过葬礼离开家庭到达坟墓,然后由此启程进入阴间世界,此处构成了两个空间过渡的门户;另一方面坟 墓作为人间的实存物,所具有的阴性特质又构成了灵魂可以暂居甚至长存的独特地域,也是那些游魂野鬼的庇护所。与墓地一样,尸体也具有阴阳、人鬼双重属性叠加的特征,这就是尸体处置能安抚灵魂的原因。在其相互关联的意义上,对尸体的处理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灵魂的存在状态,如:对尸体的清洁是为了避免灵魂将污秽带入死后的世界;装饰是因为民俗认为尸体的装裹即为亡灵在阴间的装束;安葬则是为使灵魂获得一个栖居的场所或由此处顺利进入阴间。
第一阶段初丧礼的主要任务是确认死亡,维护身体和灵魂处于合适的状态,并完成死者与生者的隔离(确保初死者灵魂的位置-维护尸体的合适状态-保证死者与生者的隔离)——第二阶段出殡和墓葬仪式的主要任务是送死者离开生者的社区,正确安置死者的身体与灵魂,促使其顺利进入死后的世界(引魂-墓葬)——第三阶段服丧和祭祀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死者的 “重生”,建构和维持死者与生者的关系(居丧-祭祀)。杰内普进而将通过仪式划分成三个阶段,其中阈限指代通过仪式中,人「脱离原来的身份而没有获得新的身份的」的生死居间的模糊阶段,三个阶段的任何环节但凡出差错,皆会产生死亡通过仪式本身的紊乱,催生「亡者归来/活着的尸体」母题叙事的民俗语境土壤。
按照象征人类学的通过仪式理论模型的「死亡——紊乱——仪式——秩序重构」的非正常死亡恐惧,完美符合理论模型中的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即为主动杜撰尸体妖魔化后的危害性,挺尸编撰防止解决措施作为传统丧葬仪式的补充,从零完美修正死者的通过仪式的终极秩序。
 artworks/21908751
artworks/21908751
其四 表象下的另一层原型:物部宫古郎女与芳香的都良香
最后这章节,暂且脱离僵尸文本回归「宫古 芳香」角色设计的话,最为令人在意的点,早在THB WIKI和东方元NETA WIKI条目中所提及:「说尸体芳香有着挖苦的意味,也有可能指因为防腐做得好所以没有腐烂」。笔者认为尸体防腐与腐败的保存情况,尸体本身散发芳香的气味这点,实在是「宫古 芳香」角色设计原型上之前无人提及的要点,特此援引神戸女子大学文学部的「田中貴子」教授所著论文《腐敗する死体——死体の表象の東西比較をめざして》:从日本的平安末期到中世纪前期,完成往生的人们的故事作为《往生传》被大量编纂,作为证明其往生的要素,可以举出尸体不会腐烂,没有腐败的味道,反而会散发芳香。另外,与此相反,无法往生或无法实现临终礼仪的死亡方式的人,经常会像通常的生理现象一样腐败。也就是说,尸体不腐烂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表现。腐烂尸体唤起了人类无法避免的不净“死”的绝对性和无常,与“九相图”和不净观有着很深的关系。
早在《往生传》类的研究中就讨论过,尸体的「ニオイ=匂い」(气味,词汇就被用来描述被认为是人类的嗅觉,包括恶臭和芳香的气味),是死者生前「德」的象征。本来生理现象中,尸体在死后开始变化,但只有实现往生的死者才会出现祥瑞。这也是平安时代末期的净土教信仰,认定逝者可以实现净土往生的标志。例如在《日本极乐往生记》等所谓的《往生传》类文本中记述的祥瑞,大致由“能听到美妙的音乐”、“西边飘着紫云”、“异香弥漫”、“光明闪耀”、“天地振动”等要素来表示,这些是表示圣众来迎接的标志,本章节特别关注「异香」即为芳香这个「ニオイ」。
在往生的标志中,紫云、光明等诉诸视觉的东西在场的万人都能互相确认,但只有异香是嗅觉这一与私人身体性有关的要素。将与个人官能相关的「ニオイ」作为往生的标志来记述的意义是什么呢?另外,身体散发芳香的不仅是往生者的特征,据吉村晶子的说法,《源氏物语》中的薰天生的体臭极其芳香的例子,身体的芳香有时会将那个人作为特别的人物圣别。在薰的案例中,她不一定等同于已经去世的人,但考虑到平安时代的贵族熟悉并迷恋香薰等物件嗅觉文化并拘泥于此,以及昂贵的香木也是身份的象征,看来「ニオイ」确实给人以积极的声誉。
先给出结论的话,尸体的「ニオイ」可以分为芳香和腐败两种,但这些「ニオイ」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死亡是往生还是凡愚众生的单纯死亡的不同。两种「ニオイ」作为各自死亡方式的证据进行对比,芳香常常与上述往生奇瑞的几个要素相结合,在人们之上表现出「不腐烂的尸体」这一特别的死亡态势。一般认为「不腐烂的尸体」与散发芳香的尸体大致同义,不仅仅是往生的瞬间,很多时候都伴随着即使过了时间也不会腐烂,保持生前的样子的记述。这意味着往生者超越「腐烂的人」这一生理宿命,成为往生的神圣之人。吉村说: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等宗教的礼仪中使用「神圣的气味」它作为特权化的「神圣的气味」发挥功用。另外,往生人的异香是往生决定的证明。
在《往生传》类型文本中,基本上往生人的尸体是不能腐朽的。尸体不烂坏、容颜不变等词语,表示尸体保持着生前的样子,决定往生。完全不能腐朽的尸体,当然也不能散发腐臭。首先,应说是《往生传》类的开端,庆滋保胤编著于公元十世纪的《日本极乐往生记》中发现如下案例:太子ならびに妃、その容生きたるがごとく、その身太だ香し。——聖徳太子;如同平安时代被定位为往生者的圣德太子尸体,不仅是散发芳香且还是和生前一样的容貌,就是「不腐烂的尸体」,可以说是圣德太子圣化的证明。尸体散发芳香这一点本来就是往生者特性的要素,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集中在「尸体不会腐烂」这一点上。与其说是特别记载芳香,不如说「没有腐败的恶臭」这样的表达越来越多。
恰好圣德太子形象被完全神化成型,就是因净土思想影响《往生传》类文本大量盛行的平安末期,估计以平安时代佛教化影响的唯一指定崇拜对象的圣德太子,死后遗体散发芳香为目标而提升自身生前品德的公卿贵族和佛门僧侣可以说是相当之多,最起码在平安末期净土思想的《往生传》类文本中「尸体散发芳香」的形容,不是挖苦的含义,更不是认为防腐做得好的含义,而是只要生前品德高尚之人,死后尸体自然就会产生各类祥瑞,完完全全就是佛教化文本的范式,特此修正以往观点。
 artworks/9785665
artworks/9785665然后,苗字片假名读音的「みやこ よしか」(宫古芳香)等同「みやこ の よしか」(都良香),苗字中间加了“の”即为对诗人的敬称/尊称;汉字转写的「宫古」等原型捏他,同时牵扯出潜藏在僵尸表象的角色设计下的两位历史人物——「都良香」和「物部宫古郎女」之间若有若无的暗示性关联性,倒是在THB WIKI的考据分析页面与东方元NETA WIKI的分析中皆有提及。
总之从旧专栏提及的内容开始,物部氏系谱上存在的「物部 宫古郎女」(みやこ の いらつめ),记载在《先代旧事本纪 天孙本纪》当中,物部宫古郎女是物部氏的女性,物部贄子和布都姫(即为物部布都原型)的女儿,也是物部御狩的妻子,物部贄子、布都姫和物部御狩都是物部尾輿的子女,物部贄子和布都姫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能多少有点难以理解,意思就是说「布都姬」与身为亲哥哥的「物部贄子」生下「宫古郎女」,「宫古郎女」嫁给跟父母同辈的叔叔「物部御狩」。
十四世孫-物部大市御狩連公。尾輿大連之子。此連公,譯語田宮御宇天皇御世,敏達。為大連,奉齋神宮。弟贄古大連女-宮古郎女為妻,生二兒。妹,物部連公布都姬夫人。字-御井夫人,亦云-石上夫人。此夫人,倉梯宮御宇天皇御世,崇峻。立為夫人,亦參朝政,奉齋神宮。弟,物部石上贄古連公。此連公,異母妹御井夫人為妻,生四兒。小治田豐浦宮御宇天皇御世,推古。為大連,奉齋神宮。——《先代旧事本纪 天孙本纪》
据日文WIKI检索到的浅显情报与文献史料姑且如此,关系性与异代婚的确令人眼花缭乱,而「物部 宫古郎女」在物部连系谱中的具体位置和地位关系的更是一团乱麻,想要理清关系笔者果断选择大阪府立工業高等専門学校「黑田 达也」教授于2016年12月17号所撰的研究纪要论文《「天孫本紀」の物部連系譜に関する復元的考察(Ⅲ)》:物部宫古郎女被认为在物部氏尾张连系谱,在这系谱中,如果援引《天孙本纪》中的物部目为物部御狩和物部宫古郎女(御狩兄弟贄子の女)成为异世代婚姻的话,物部目应和物部守屋、物部惠佐古成为同世代,以物部马古为物部目后代的《天孙本纪》物部系谱还是没问题的,就是物部御狩-物部目-物部马古的位置无需改动。
但物部宫古郎女是不是物部目生母的情况是存疑的,通常物部宫古郎女被认为是物部目的生母,而第十五代的物部大人与物部目被认为是同辈的麻吕(兄弟),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认为新的物部目父亲的「物部御狩」和「宫古郎女」的异世代婚姻,都是基于原来的物部目的父亲「物部大人」和母亲「有利媛」的基础上的。宫古郎女由物部麻侣的生母改动成物部目的情况,由物部目由物部木莲子的孙子改为相当于曾孙一代的尾舆孙,物部马古和宫古郎女避免自己成为比后者大一代的异世代婚姻,以及改动为物部目生母的必要性,但无论哪一个都很难认为是比留下物部宫古郎女作为物部麻侣的生母更重要的事情,物部麻侣没有记载生母,而是记载在曾祖父物部大人和祖父物部目。
敢于主动改动生母与后代关系的物部氏尾张连系谱,或是为豪族内部的政治性地位考虑?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交界处的物部氏尾张连豪族群体内部的血脉复杂程度,笔者还是觉得不要以通常辈分词汇去称呼,而是分为同代婚姻与异代婚姻的且从系谱中的可疑点还是可以看出物部氏在尽全力避免同代婚姻多以异代婚姻为主,唯一不变的自然还是近亲血缘的繁衍。
之后,来看看「宫古郎女」的姓氏苗字,物部氏为被纳入系谱后赋予的豪族姓氏不考虑,后面的「宫古郎女」(みやこ の いらつめ)中的「郎女」(いらつめ),前者「宫古」(みやこ)其汉字表记还可以写成「都古」「宫子」或「都」,考虑到物部宫古郎女活跃的古坟时代后期至飞鸟时代前期的时代背景,「みやこ」应是早期都城/宫殿的名称引申而来的语源取名,汉字转写表记的「宫古」皆为物部守屋时期的物部氏编撰系谱时增补?后者「郎女」在记纪文本天生具有的尊称/敬称含义,同样类型还有男性用的尊称/敬称的「郎子」,「此郎女」是在《古事记》中下卷文献史料中常用的敬称。
据学習院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日本語日本文学的「中野谦一」老师所撰的《古事记中下卷的敬称》:「郎女」为敬称的女性也可认为是以皇女、后妃为基准的人物。在《古事记》中的「郎女」是皇女、后妃以及与其余相同地位的女性,「郎女」与其他敬称的关系来看,就是仅限于「命」或者「王」的交替使用的案例。近似于「郎女」的敬称一样,存在除却豪族的系谱编撰记述以外也能看到的人物,允恭天皇的皇女有三名「大郎女」,这里的「大郎女」不一定表示长女,但可以认为大、若表示某种长幼关系。「郎女、郎子」虽具有「王」所不具有的性别表示功能,但如果不能向皇族表示相应的敬意,而《古事记》避免使用也是理所当然的,皇族和非皇族的识别对《古事记》来说是重要的问题,那么对豪族、氏族出身者也使用的敬称,至少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无力的。
就是说,「郎女」这一称呼在文献史料典籍与豪族、氏族系谱,针对古坟时代晚期至飞鸟时代中期的女性贵族人员敬称/称呼的泛化,在奈良时代变化为天皇皇族群体避免在《古事记》等文献史料使用,逐渐沦为豪族、氏族在本家豪族编著系谱时给豪族内部女性人员上敬称的必要步骤,而「物部 宫古郎女」的姓氏苗字,「物部氏」与「郎女」皆是豪族内部所赋予的称呼,非正式的氏族内部日常场合的说不定就直接称呼「宫古」罢?
 artworks/32605192
artworks/32605192在《東方求闻口授》中对于芳香的一设补充中,ZUN借由在阿求角度记述中,提到过一段话:但是我想她还存在一些生前的记忆吧。当撕去符咒,从邪仙的咒缚中解放后,似乎她就会回到生前的行动模式吧。曾经在空旷墓地那如同毯子一般铺满地面红叶上,看见她呆然站于其处的,咏唱着诗歌的身影。稍微有些被吓到呢。 可以说,ZUN笔下对于都良香(みやこ の よしか)的补充捏他到此为止,而在笔者检索阅读过关于持有「芳香原型可能参考都良香」观点的诸多专栏当中(包含笔者的旧版芳香专栏),几乎存在某种试图身为汉诗文人的都良香和道教上扯上关系?譬如罗城门对诗的「气霁风梳新柳发 ,冰消波洗旧苔须」,还是近江国竹生岛的「三千世界眼前尽,十二因缘心里空」,甚至营造出都良香身在官场却一心修道,最后弃官隐居成功在大峰山得道的传承文本。笔者要强调的是,都良香吟诵汉诗倾慕仙道的事迹的确很洒脱没错,无非是历朝历代的后世文人给都良香编造后赋予的文本,而在史实文本记述中的都良香形象又是如何呢?都良香和道教到底有无关系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的「李育娟」副教授于2013年刊登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所撰的日本古典文学论文《論平安文人都良香之形塑與唐代文人軼事之關係》文中认为:都良香的逸闻传奇则具灵异色彩的「罗城门之鬼/罗城门对诗」,首见于《江谈抄》,而后世的《北野天神缘起》、《十训抄》、《撰集抄》、《体源抄》、《神道集》、《本朝一人一首》、《本朝语园》、《谣曲‧实盛》、《日本诗史》、《史馆茗话》等皆可见相关的记载或衍生的诗话。「气霁风梳新柳发,冰消波洗旧苔须」原收于《和汉朗咏集》卷上〈早春〉,《江谈抄》记诗题为〈内宴、春暖〉。依据《日本三代实录》的记载,内宴举行的时间为元庆二年(878)一月二十日:「廿日丙辰,内宴,近臣赋诗及奏女乐,群臣欢洽,毕景而罢,赐禄各有差。」另外,菅原道真的家集《菅家文草》,则收有当日为内宴所撰的诗序。鬼出现的地点罗城门,也可以写作罗生门,是平安京的正门。「罗城」指围绕都城的外郭,中世类书《拾芥抄‧宫城部》记载「罗城门」为「二重门七间」,可知城门是二层构造,颇具规模的建筑物。另外,都良香的竹生岛接下句范式也流传极广,故老传云都良香所撰〈晚夏参竹生岛述怀〉一诗中,「十二因缘心里空」句非他本人所做,而是受竹生岛神明弁财天指点而成。
文人都良香虽然被大江匡房列入神仙之列,但实际上他与神仙思想的交涉并不深。都良香除了写过神山的《富士山记》,及以神力击退恶鬼的法师传记〈道场法师传〉外,与神仙思想有最直接关联的便是《神仙策》一文。这篇《神仙策》是他应试时,试官春澄善绳所出的考题。另一篇《弁薰莸论》却透露出他本身对成仙不抱兴趣,而松田智弘也同样指出都良香的神仙故事应是后世附会的。
此外,都良香其实是虔诚的真言密宗信者。在《扶桑略记》中也收载了都良香的史传,前半的记述与《日本三代实录》相同,后半则叙述都良香的宗教信仰。他潜心学习真言密教,师事东寺的僧正真然和尚,日日勤于念佛:「驿思空门,雅信佛理。于时僧正真然住东寺,良香就受真言密教,一遍而记于心。虽勤学业,不废念佛。年四十六卒。」都良香的生涯中与神仙道教的牵涉极为薄弱,可见大江匡房在神仙传中描述他学仙求道之事乃是虚构。不过在仙传中构筑出的都良香形象,倒是与唐代的文人有共通之处。
在平安朝,佛教才是皇家、贵族、庶民的信仰中心,在贵族社会里净土信仰与密教修法同时并存,称名念佛与往生净土亦大行其道。自第一个出家的宇多法皇起,陆续有不少天皇选择出家成为法皇。佛教与平安贵族生活圈紧密结合,渗入贵族社会的生态与文化的底层。日本虽然有混合中国道教术法、杂密而成的修验道,但接触者多是山林的修行者。
一般文人、贵族对神仙思想的认识,多来自于中国的传奇志怪等小说;对术法的理解,则来自于杂密、阴阳道中所吸收的道教术法。即使是对神仙思想深感兴趣的大江匡房,他所写的第一部日本神仙传记《本朝神仙传》,成仙者泰半是僧侣或修佛之人,或是像都良香、橘正通等平安朝的文人。
在佛教全盛而神仙道教氛围薄弱的社会,道士、道观皆不存在,道教仙术一般人难以接触。大江匡房笔下文人修练仙法的情节,其实缺乏社会文化的基础。就如平安文人模仿中国游仙诗以神仙为题入诗一般,都良香的修仙情节,也是模仿唐代文人修仙行为的产物。


传说京都城门上住着鬼的最早记载来自《江谈抄》和《本朝神仙传》。自此之后,世间便开始盛传罗城门或朱雀门是鬼的栖身之所,相关的传说在后世的说话集中不断地被转载流传,故事情节也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生变化。比较收录在《江谈抄》、〈朗咏江注〉和《本朝神仙传》中的都良香逸闻,可发现分述在《江谈抄》「故老传云」的轶事,被大江匡房统合在《本朝神仙传》中,成为一部完整的都良香传说。罗城门位于平安京朱雀大路的南端,罗城门作为划分洛中和洛外的边界,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以防止侵入都城的鬼和疫病,罗城门自古以来作为边界场所的认知是存在的。
都良香史传中的性格、事迹甚至是宗教信仰,和大江匡房所经手的都良香传说,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民间的传说常不符史实,但即使浮夸、荒诞不经,也必有脉络可寻。在都良香逝后,至大江匡房的作品问世之前,没有出现都良香的传奇故事,但在《本朝神仙传》、《江谈抄》之后,相关传说却大量涌现,并不断地被转载在后世的说话、缘起、诗话、谣曲等文学作品之中。
大江匡房将改编过的都良香传说,分述于不同的著述:《江谈抄》、《本朝神仙传》、〈朗咏江注〉之中,并以故老传说的形式,营造出口耳相传的氛围,将自己化身为街谈巷说的记录者。透过模糊撰写者的处理方式,成功将中国的传说转化成平安文人的趣闻轶事。综观大江匡房所写的诗话作品,其背景大部分是以《和汉朗咏集》、《本朝文粹》收录的诗文为主,研判他可能以当时日本的诗文总集为中心,选择他需要的篇目,再参考中国诗人轶事,从中取得灵感进行改写。
到此为止,史实都良香与文本都良香的确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后者的文本都良香说是大江匡房一股子复制唐代文人事迹进行再创作的结果也不为过,前者的史实都良香唯独创作出的汉诗和歌和著作是真实,这就是传统历史语境与虚构历史语境常见的情境:「历史上的确存在这人,但事迹文本和传奇皆为后世文人赋予创作的,产生史实形象与民间形象的割裂」。在这之外,兴许就剩下受到镰仓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中世由菅原道真的天神信仰影响,变相贬低「都良香」作为宫廷文人素质的《天神缘起》型文本。

平安末期的藤原兼实与大江匡房共同编撰的《江谈抄》中的「都良香罗城门与鬼对诗」,说明罗城门之鬼这时期还没和「茨木童子」联系上,而是作为凸显都良香胆识和文采的罗城门境界本身他者化的象征而已,即为「诗成泣鬼神」。在《都良香像の変質と「天神縁起」 》中则认为都良香汉诗可感动鬼神的灵感源自平安前期编撰的《古今和歌集》序文:力を入れないで天地(の神々)を感動させ、目に見えない鬼神をもしみじみとした思いにさせ、男女の仲を親しくさせ、勇猛な武士の心を和らげるのは、歌なのである。却在上述论文中认为是大江匡房在平安末期借鉴引用贺知章和杜甫两者均夸赞李白诗歌可以泣鬼神的结果「此诗可以泣鬼神矣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毕竟大江匡房所接触的都是当时平安宫廷文人不太接触的唐宋笔记小说和逸闻趣事,所认为相较于《古今和歌集》的序文,取材自李白传说文本的可能性更高就是。
沦为都良香陪衬的「罗城门之鬼」和「渡边纲退治茨木童子」的传承又是如何混同的?后者渡边纲退治茨木童子的文本,茨木童子在化为妇人争夺走断臂后逃走的地点,不同版本均有不同的说法,文本发生在大江山酒吞退治前的点就是一条戻桥,文本发生在大江山酒吞退治之后的地点则是罗生门(罗城门),据文本发展时间判断早期版本应当视为一条戻桥,罗城门版本则完全是日本中世以来的谣曲创作文人的导致逸闻混淆的,当时本来没有关系「罗城门栖息之鬼」的传承与「渡边纲退治茨木童子」的传承文本完全是被同一化而已,至于「罗城门之鬼」也经常被视为与茨木童子相同,实际上应当是罗城门境界所幻化之鬼,另有说法认为是罗城门上放置的毘沙门天像的抽象变体。
《今昔物语集》假名序文形容——夸赞李白诗歌足以感动鬼神的轶闻——大江匡房创作参考《江谈抄》《本朝神仙传》的都良香罗城门对诗「気霽風梳新柳髪,氷消波洗旧苔鬚」——中世谣曲罗城门版的「渡边纲退治茨木童子」——两者混同后在鸟山石燕笔下产生的《今昔百鬼拾遗》「都良香与茨木童子对诗」景观。
 artworks/101251244
artworks/101251244
其五 圣地巡礼
倘若要问笔者在完全「宫古芳香」角色原型文本的上述解析后,会给各位推荐什么角色原型巡礼地的话?很遗憾,这次并不能增补两三个强关联的芳香原型巡礼地,取而代之的话,则是对于旧版芳香专栏推荐的契合「都良香」原型要素巡礼地——罗城门遗址的情报补全,再者就是ZUN的神灵庙访谈中提及的奠定港式「灵幻僵尸喜剧」开山之作影片风格的《僵尸先生》取景地的二次巡礼地,即为电影中九叔开棺作法之地?这好歹是芳香角色设计原型的直接来源,更是香港唯一的东方原型角色关联的原型巡礼地。
京都府京都市南区
羅城門址
(羅城門遺址)



所在地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南区唐橋羅城門町54(花園兒童公園內)
交通方式:近铁京都线「东寺」站徒步12分、京都市营巴士「罗城门」站下车徒步1分。
东方关联角色:宫古芳香、茨木华扇
原型捏他:都良香罗城门对诗的事迹典故
追加情报:安置在东寺宝物馆的兜跋毘沙门天造像被认为是放置在罗城门的造像,在春秋两季公开展览的东寺宝物馆,还可欣赏到当年罗城门上放置的兜跋毘沙门天造像;JR西日本京都站北侧的「メルパルク京都」前面放置平成六年(1994年)为庆祝平安迁都1200周年,使用一亿日元全面复原的平安京罗城门十分之一模型。

香港特别行政区
西贡区大埔区交界处
马鞍山郊野公园
黄竹洋村
《僵尸先生》取景地


所在地地址:麦理浩径第四段(建议谷歌地图输入下列经纬度数据:22°24'01.2"N 114°16'14.5"E)
交通方式:港鐵觀塘線鑽石山站乘坐92號巴士或者彩虹站乘坐1A小巴前往西貢碼頭,徒步一小時前往《僵尸先生》取景地。
东方关联角色:宫古芳香
原型捏他:《神灵庙访谈》中ZUN提及的宫古芳香灵感的原型电影《僵尸先生》的取景地
追加情报:在香港电影业界野蛮生长的七十年代多部经典电影在此地取景的草地已经被郊野公园消防设施所占据,好在《僵尸先生》拍摄英叔针对棺材作法的草地还在消防设施的围栏内,电影中同款的景观视角还未被毁坏。

 artworks/37018656
artworks/37018656 artworks/19009579
artworks/19009579结语:原本的芳香重制专栏是打算直接接续到青娥重制专栏之后的,但没想到不可抗力+突发情况,硬生生拖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只能说总算把怨念之物给重制完成,本以为芳香重制的各方资料或参考论文相较重制青娥专栏时较为轻松点,属实是没想到芳香重制的大纲越整理越多,这就不得不另开篇幅全面重制改动,而非以往的小增补几百字的重制,总之希望权当素材库重制的两篇专栏中,试图发掘出什么值得青娥x芳香产品二创的点罢!最后请各位欣赏芳香额头上的黄符符札!
 artworks/6240771
artworks/6240771【相关文章】
本文地址:http://www.yesbaike.com/view/145116.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